李振城 | “宝船”的历史真相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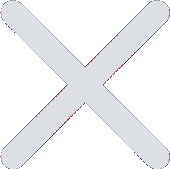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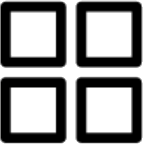
关于郑和“宝船”的真实面貌,长期以来学术界与公众之间存在诸多误解。中国郑和研究会副秘书长赵志刚教授表示,要厘清“宝船”的本质,必须从历史文献、考古遗址与文化语境等多方面展开系统考察。
首先,“宝船”一词并非始见于郑和时代。在佛教语境中,它象征渡人出苦海的灵船;而自宋代起,装载瓷器、丝绸等贵重货物出海的大船,也常被称为“宝船”。这一用法延续至明清两代。如明代出使琉球的柴山在其碑文中记载:“特敕福建方伯大臣重造宝船。”至清代,徐葆光出使琉球,其船仍被当地人称为“宝船”。
ADVERTISEMENT
地名亦是宝船文化流传的实证之一。天津“宝船口”正是因永乐年间平江伯陈瑄巡视所泊大船而得名。《新修长芦盐法志》中记载:“宝船口,在天津城东南五里……泊巨舟于此。”至今地名未改,成为明代海外贸易与造船文化的活化石。
随着时代推演,公众逐渐将“宝船”一词与郑和船队中最大型船只画上等号。然而,《瀛涯胜览》等明代古籍中,“宝船”多为泛指,既包括郑和船队的旗舰,也包括其他出使或海贸船只。并非专指一种巨型战舰。
围绕“宝船”最大尺寸的争议,则更为复杂。据马欢《瀛涯胜览》钞本、谈迁《国榷》和《明史》记载,宝船可达“四十四丈四尺,阔一十八丈”,换算为长约137米、宽达56米。如果确凿无误,这将使宝船跻身世界最大木船之列。但这一数据并未出现在《瀛涯胜览》的最早版本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室主任万明教授指出,《瀛涯胜览》中关于尺寸的记载,很可能是后人增补。其一,文本中“监丞”排位居于“少监”之上,违反明代官制;其二,文中出现《大明一统志》的注释,而该书成于天顺年间,晚于马欢原作时间。可见,大宝船的尺寸并非马欢原笔,而是后人加工。
为何后人要“润饰”宝船?学界普遍认为,与明中后期国家衰弱、倭寇横行、海禁严厉有关。嘉靖年间,社会普遍怀念永乐时期的国威盛世,赋予郑和宝船更强烈的民族象征。鲁迅与向达皆曾指出,罗懋登撰写《西洋记》,正是“倭患甚殷、当局柔弱”背景下,以文学方式寄托对强盛国家形象的渴望。
而从第一手资料来看,许多明代学者虽记述郑和航海细节,却未提及宝船尺寸。如祝允明的《前闻记》、黄省曾的《西洋朝贡典录》、以及《星槎胜览》《西洋番国志》等史料,皆未描述具体船型或大小。说明“巨型宝船”这一形象,很可能是后人理想化的产物。
赵志刚教授长期参与宝船厂遗址的发掘工作。据他介绍,龙江船厂遗址曾出土数以万计的造船构件与航行器具,包括巨型舵杆、船钉、铁锚等。其中最大的一件铁锚高达2.7米、重逾一吨,爪距约2.4米,构造复杂,磨损明显。这些遗物清晰表明:明代确有建造并使用大型远洋木船的技术与能力。
同时,明代文献也提供线索。《明仁宗实录》记载,明仁宗即位次日即下令终止下西洋活动,“宝船悉皆停止”,原泊福建、太仓者须回南京。大量舰船因而返泊龙江与宝船厂,成为今日遗址考古的基础。
赵志刚教授指出,历史的真实,往往比想象更复杂。“宝船”作为文化符号,其含义远不止于“最大号战舰”。它融合了宗教象征、航海工具、朝贡制度与民族记忆,在数百年间不断被重构与再诠释。
ADVERTISEMENT
热门新闻





百格视频





ADVERTISEMENT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